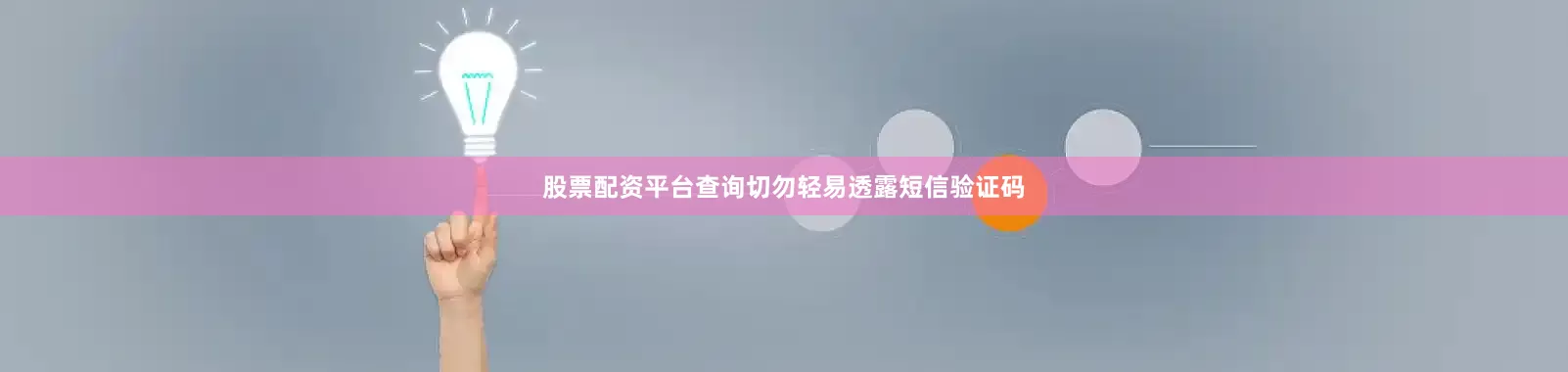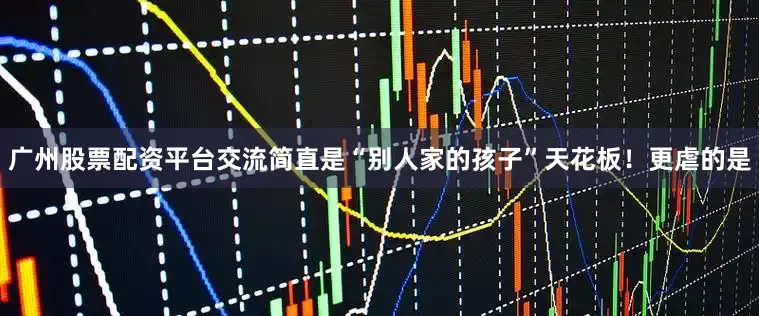配资实盘平台相互盯着对方手里拿着的报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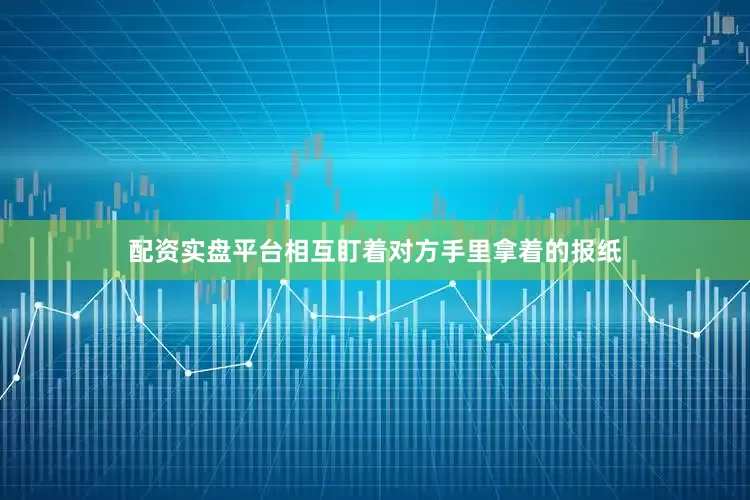
北平和平解放背后的关键人物,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,本本可以借此功绩爬升到更高的位置。
可她偏偏走了一条出乎意料的路:拿起笔当起了记者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西南联大来的富家小姐
在昆明的雨季时节,西南联大的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地都是学生。
傅冬菊坐在最后一排,手里握着新买的《新华日报》。这个女孩的父亲在华北掌控着重要的兵力,家里既不缺钱,也不缺地位。

周围的同学都清楚她的来头,有些人羡慕得直流口水,有些则敬而远之,生怕惹上麻烦。
她和别人心里的想法完全不像。
每到假日,傅冬菊总会跑到《新华日报》编辑部,那儿聚着一帮关心国家未来的人,空气中满是油墨和烟草的味道。
有时候,周总理会走过来和年轻人聊聊天,会问他们在看哪些书,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意见。
傅冬菊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时候,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周伯伯”。

周总理立马提醒说:“叫周叔叔吧,你爸比我大三岁。”
这个细节让傅冬菊记了一辈子,要知道,有些东西真比身份还要重要。
周总理之后还说过一句话:冬菊,你能帮帮你父亲搞搞工作吗。
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,悄悄埋在了心底。
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,可没按照父亲的意愿出国深造。傅作义找人帮忙搞定了护照,还请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帮忙安排一切。

傅冬菊眼前的路特别明白:去美国读书,脱离战乱,避开危险。
傅冬菊就没打算答应。
她对父亲讲:在国内,我能为国家干不少事。
这话听着挺轻松,可是真做起来自难度挺大。傅冬菊应聘到了天津《大公报》,当起了记者,在副刊编辑那块儿,开始写些“别人不敢发表的激进文章”。
报社的老编辑一眼就发现了啥端倪,傅作义也隐隐觉得女儿可能和共产党扯上关系了。
父亲又一次劝她去国外,但傅冬菊还是坚决说不。
她悄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,入党时,介绍人李定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作暗号,敲开了傅冬菊的门。
她一开门就愣住了,撞见的人竟然是自己在西南联大结识的老同学,叫周毅之。

他们站在门口,相互盯着对方手里拿着的报纸,随即都笑了起来。
那一瞬间,傅冬菊多了两重身份:一是傅作义的女儿,二是党员。
这两种身份,注定会在某个时候碰出火花。

中南海里的女儿
辽沈战役一打响,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让人跑到天津,找到了傅冬菊。
任务定得清楚明白:赶紧回到北平,把爸爸的事儿搞定。
傅冬菊整理好行李,乘火车回到了北平。她搬进了中南海的居仁堂,傅作义睡在外屋,女儿则住在里屋。父亲担心女儿会乱跑,每晚都会确认她是不是还在房间里。

表面上来看,这其实就是个女儿回家探望父亲的场景。
其实,傅冬菊每隔一天都得去东皇城根胡同那边一个地下党员家串门,跟组织的联系人碰个面。
她把父亲那些情绪上的变动,比如叹气、咬火柴头、发脾气,甚至有想自杀的念头,全都记在脑海里,然后一字不漏地汇报给上级。
这些信息很快就传到了战场指挥中心。
聂荣臻后来还说过,你们对傅作义的动向掌握得太精准了,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,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,上午出事的事,下午就知道了。
在战争史上,要能这么精准地掌握敌方最高指挥官的情绪变化,真是少见得很。
傅冬菊正在干一件挺危险的活。

她明白得很,父亲身边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。军统、中统的人在北平肆意横行,傅作义能操控的范围其实也挺有限的。
每次出门会见人,她都得提前想好说辞,甚至得精确算好时间,免得被父亲发现端倪。
有一天,傅作义问他女儿:“你是不是属于共产党啊?”
傅冬菊说:“我哪配得上。”
这话听起来挺含糊,既没明确承认,也没否定。傅作义一直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,也没再说什么。
父女二人心里都明白,彼此都在默默扛着压力,没有多说一句。
转折就发生在济南战役之后嘛,华北的国民党部队和南线的联系终于断了,傅作义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。
蒋介石让他把福建列为后方基地,准备撤退的安排就这么定了。

傅作义在华北打拼了二十年,手底下有几十万军队,这些人要怎么安置呢?
他逐渐开始心猿意马,态度也出现了变幻。
傅冬菊抓住这个好时机,告诉父亲自己有个同学和共产党有关系,而且这人绝对靠谱。
傅作义皱眉问道:“是正统的共产党,还是军统的?”提醒对方别被迷惑了。
傅冬菊说:“是我同学,确实是正统的共产党。”
傅作义又问:“是毛主席安排过来的,还是聂荣臻派过去的?”
傅冬菊一时想不出答案,第二天就去找组织问个明白。佘涤清告诉她,就说是毛主席派来的。
傅作义听完这些话,沉思了许久,然后让女儿帮忙给毛主席发一封电报。

这份电报不能写在纸上,只能牢牢记在脑海里。傅作义口述了两遍,让女儿反复复述了两遍。
傅冬菊把那封电报带出了中南海,来到东皇城根时,感觉就像走了半辈子那么悠长。
电报发出之后,和谈也就随之开启了。

改名换姓的战地记者
北平和平解放那天,傅冬菊没留在北平享受那喜盈盈的胜利场面,她回到天津,将名字改成了傅冬,还在《进步日报》做起了副刊编辑。
从那之后,许多人都不清楚这个身世柔弱的女编辑,竟然是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人物。

她不想被大家记住,更确切点说,她不希望被当成“傅作义的女儿”。
几个月之后,傅冬菊加入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,坐着敞篷车,跟着大军一路往南走,经过南京、武汉,最终抵达了昆明。
那个曾经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女孩,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城市,可是现在的她,身份完全变了样。
她变成了个战地记者。
在昆明,傅冬菊帮忙创立了《云南日报》。她走访工厂和农村,采访工人以及农民。
这让傅冬菊觉得,她做的事情挺有意义。

后来,陈赓把傅冬带到北京,准备安排她去朝鲜战场当翻译。
傅冬菊是学英语专业的,在西南联大学习的就是这门课程。去前线担任翻译,听着挺合适的安排。
帅孟奇一看见傅冬菊,心思就变了。
她觉得前线太危险,觉得这瘦瘦弱弱的女记者不太合适。最终的选择是:留在人民日报社。
傅冬菊就这么加入了人民日报。

她也变成了个普通的记者,和其他同事一样,拿着采访本,坐火车四处跑新闻。
没人特别照顾她,也没人因为她是“有功之臣”就看得比别人高一档。
傅冬菊从不提自己以前的事,总是专注于写文章。
大家对她的评价是勤奋踏实、谦逊有礼,真正热爱新闻行业。
有人不明白,还问她为什么不去做更重要的事。
傅冬菊不仅直截了当地表示:我喜欢新闻,没有其他复杂的解释。

傅冬菊这么说,实际上藏着更深的意思。她很清楚,她所做的那些事情,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,不用每次都提来提去。
她宁愿当个见证人,用笔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。
她和丈夫周毅之结了婚,有三个女儿,日子过得挺朴实平凡,没有啥特别的亮点。
周毅之也在人民日报工作,俩人平日里都在外地采访,见面的时候也不多。
傅冬菊一直不跟孩子们提起自己的过去。
直到女儿们长大以后,才知道母亲曾经干过那么了不起的事情。

一辈子只做一件事
多年以后,有记者问傅冬菊:要是当年听父亲的话,去国外留学,会是什么样子呢?
傅冬菊想到这事儿,回应说:要是还能重来一次的话,我依然会留在国内。

傅冬菊想了想,轻声说道:要是能再来一次的话,我还是会留在国内。
她一直没有感到后悔。
傅冬菊到了晚年,生活过得挺简朴,大部分存款都捐给了希望工程。
有人劝她留下点钱给子女,傅冬菊笑着摇头:她们有双手双脚,自己也能过得去。
这个曾经靠着功绩晋升高位的女人,整辈子都在干一件事:用笔写下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。
她没有提到自己在北平和解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。

后来同事们才从其他地方得知,这个身形瘦弱的女记者,竟然经历过那么惊心动魄的事情。
成绩不是用来夸耀的,干活才是最要紧的事。傅冬菊用一辈子证明了这个道理。
她没有去追求高官厚禄,也没有选择安稳舒适的生活,而是坚持在最平凡的岗位上,用笔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2007年,傅冬菊在北京去世,享年83岁。
讣告一发出去,才让不少人再次了解到她的身份。原来,这个一辈子当记者的女士,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,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她留下的,不仅仅是那些新闻稿件,更是一种永不过时的精神风范。

一个人要么靠着成绩赢得许多好处,要么就放下这些,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
傅冬菊坚持走的是后者,用一辈子去实践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。
她的墓碑上没留任何职位的名字。
只有个名字——傅冬。
这两个字,代表了她一辈子的答案。
这两字,象征了她一生的答案。
专业股票配资知识论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